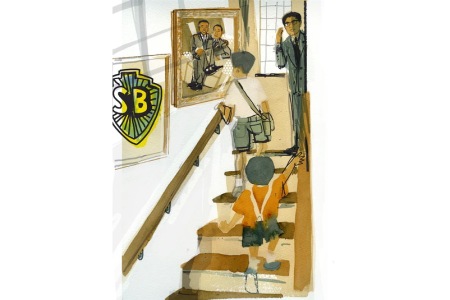Archive for the ‘蔡瀾’ Category
蔡瀾 – 活一天過一天的人生 蔡瀾斷捨離 Part 2
2024/05/02蔡瀾 – 活一天過一天的人生 蔡瀾斷捨離 Part 1
2024/05/01蔡瀾首次來馬辦書畫展鍾楚紅親臨現場見證
2023/09/02(八打靈再也2023年09月01日訊)

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瀾,第一次來馬來西亞舉辦個人書法展,香港一代女神鐘楚紅(紅姑)也親臨現場,見證好友的書法展開幕!


基於蔡瀾行動不便,所以他在助理的陪同下,於上午11時許坐輪椅抵達星洲日報總社禮堂,為其「草草不工」慈善書法展進行開幕儀式。



這也是蔡瀾首次在馬來西亞舉辦個人書畫展,書畫展是於上午11時舉辦,這場活動也吸引許多慕名而來的民眾前來觀賞。
這場書法展是由檳威華團聯誼會、蘋果旅遊集團及青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聯辦,星洲日報為協辦單位,即日起至星期日(9月1至3日)在星洲日報總社禮堂舉行,現場共展出蔡瀾的128幅書法作品。


身為食神的蔡瀾於今年3月23日宣佈因抱恙而暫停更新數日,他今日出席「草草不工」慈善書法展開幕禮時,向在場的嘉賓及民眾娓娓道來,他在4月中跌倒的事故。
「當時是老婆不慎跌倒,而我在上前營救老婆時,自己也不慎摔倒,還把骨頭摔碎,於是就入院做手術。那段時間是真的很痛苦,很慘。」
他表示,當時治療需要服用大量藥物,一粒不夠就吃兩粒,將藥物當成花生那樣來吃,語畢莞爾一笑。
經歷跌倒事故後蔡瀾的容貌明顯比以前蒼老。
「如今想起那段經歷依然會很痛,無論是生理或是心理,但不去想就不會痛。」
交代好其跌倒事故後,蔡瀾便說:「我不習慣自己講,我喜歡別人問我問題,我再回答。」
隨即便有觀眾舉手提問他,如果再見已故黃霑、倪匡和金庸,會對他們說甚麼,蔡瀾立馬爆粗說:「X你老X,走得那麼快,沒有等我。」,不止現場出席者大笑拍掌,就連坐在席上第三排的鐘楚紅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接著有民眾詢問最喜歡甚麼美食時,他稍加思索後坦言,喜歡馬來西亞的炒福建面和榴槤,喜歡香港的燒臘和叉燒。
當被詢及身為一名長者的他,會給年輕人甚麼忠告時,他也笑言,沒有任何忠告要給年輕人,過一天就是一天,唯一的忠告是有時間就多閱讀書籍,少玩遊戲機。
威華團主席拿督王金華表示,雖然他本身是一名生意人,但對文化特別敬重;「蔡瀾先生是我的偶像,我就是他的粉絲。」
「也許有些人會感到很奇怪,為甚麼威省華團聯誼會來到雪隆?說起來,一切都是機緣巧合,我們和蔡瀾先生在4年前就計劃在檳城舉辦一場書法展,無奈在冠病疫情的籠罩之下,導致活動被擱置,最後才決定在雪隆舉辦。」
他說,我國政府要打造一個昌明的馬來西亞,該聯誼會是樂見其成的,同時他也認為政府除了提升國內物質水平之外,在文化和藝術方面也必須給予更多的關注。
「政府可以透過各種獎掖和資助,為國內的文化及藝術領域奠定基礎,確保物質和精神發展能齊頭並進。」
他說,他在蔡瀾的身上看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暉映成趣,蔡瀾從人間煙火吃出了飲食文化,又從影藝書法檢驗了現實生活,這一點是值得大家去學習的。

出席者包括蘋果旅遊集團首席市場總監黃引輝、連城畫廊主席拿督沈哲初、青城文化總經理何慕傑、星洲媒體集團執行董事兼集團首席執行員黃康元及副執行總編輯鄭丁賢等。
來源: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三先生
2020/12/23唸初中時到了周六常到父親的辦公室,等他中午放工一齊去吃飯。
那是一棟三層樓的大廈,位於新加坡羅敏申路,是邵氏公司的辦公室,一樓是發行部,堆滿了等着輸送到各家戲院放映的一盒盒圓形鐵盒菲林。
父親說,那叫為拷貝,由英文的copy一字音譯過來。一個盒裝了一卷一千呎的底片,每部電影大概有八千呎。經過發行部,有條樓梯,爬上了二樓是中英文職員的辦公室,家父就在那裏工作。
樓梯旁邊的牆上,掛着一幅巨大的照片,已有點發黃,那是邵逸夫先生和他哥哥邵仁枚先生在上海影樓拍的照片,邵仁枚先生在邵氏家族中排行第三,大家都叫他三先生。
真是奇怪,兩位已經成年,穿着西裝的人,還像小孩子一樣,小的坐在大的膝上,在當今,只是同性戀者才肯做的姿式,可以看見兩人的關係,是那麼親密的。
幾個世紀後,我再到現在的邵氏大樓找這張照片,管理邵氏資料室的是六先生的孫子Chistopher,我問他找不找到這張照片,他回答沒有印象,見也沒見過。
我還問他有無兄弟們往來的信件,他也說不知道放在那裏了。如果能夠尋覓,那才是邵家歷史最珍貴的資料,因為兩兄弟即使不見面,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書信來往,六先生來了香港發展後,三先生寫給他弟弟的信,由家父負責,爸爸是一個完全能夠守密的人,一些事只告訴了我,他也知道,我遺傳了他的道德修養,不會講給別人聽。
家父說他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感情那麼深的兄弟,一切無所不談,包括最秘密的男女關係和健康狀況,連最輕微的傷風感冒也談個不停。
我不問,家父當然也不會提起,我是一個不談別人私隱的人,偶而和家父聊的,是三先生如何互相援助他弟弟的往事,像邵氏片廠在別人眼中,總是風光,但背後也有不順利的往事,製作的片子有個時期一部接一部地在票房中失收,三先生由新加坡把錢匯過來,一筆又一筆,至到有個年代要把房地產拿到銀行抵押,才能填滿邵氏片廠無底的洞。
那種兄弟情是當今前所未有的,已經沒有任何事可以將兩人的情份拆開。他們之間,還有一個最後的堡壘,那是在日本東京的銀行開了一個戶口,把最值錢的地契、鑽石和富克蘭金幣都存進那個保險箱中,那是兩人最後的防線,互相答應不會去碰它。
六先生偶而也會向我提及他們兄弟的事,像兩人最初都替他們的大哥邵醉翁所創的「天一」片場工作,六先生十幾歲時已拿着又重又大的攝影機到處去拍新聞片,剪輯之後,在正片之前放映,有甚麼重要的事件或災難,都會出生入死地跑去記錄下來。
六先生後來又向一位叫徐佔宇的攝影師學習,開始在一部叫《珍珠塔》的戲擔任了大部份的攝影工作,可是當電影上映時沒有他的名字,這時開始了他想脫離「天一」公司的決心。
「天一」在上海電影界冒出後,名字叫「天一」,有「天下第一」的意思,惹起其他電影公司的杯葛,趁這機會,他們兄弟向大哥邵醉翁提出,把《珍珠塔》這部片子拿到新加坡去,打開那邊的市場。
想不到去了新加坡,也遭受到其他發行公司的包圍,沒有人肯把戲院讓他們放映,兩兄弟就租了一輛貨車,把片子拿到鄉下,架起銀幕,在露天放映起來,大受歡迎,六先生常提起此事,自豪得很。
因為所有事都親力親為,性子又急,各地方跑來跑去,在星馬嘛,說英語的人多,總得取個英文名,六先生就叫自己跑跑Run Run,而三先生的中文名仁枚,也順理成章地叫為Run Me,這兩個字用上海話讀起也適合。
至於邵這個姓氏,英語拼音應該是Shao,六先生認為外國人記起來沒那麼容易,反正大家都知道有個叫Bernald Shaw的文豪,不如就改成Shaw吧。
而到了南洋,不講英語不行,六先生和三先生一齊勤學起來,報了一個英文班學習,六先生告訴我:「最初班裏有很多人報名,我排的是三十五名,輪到我報出姓名時,我忘記說是邵逸夫,My name is thirty-five卻衝口而出了。哈哈哈。」
有了英文名字,便得有英文招牌,好萊塢大公司有華納兄弟,招牌是一塊盾牌,兩兄弟照抄,也用了一塊盾牌。不怕人說抄襲嗎?六先生回答「不是抄,是借用。」
大華戲院和大世界
2020/12/16我們一家與邵氏兄弟的關係淵遠,家父蔡文玄到了南洋之後就受聘於邵氏,當中文部經理,所謂經理,也是一腳踢,總之任何有關中文的事都得處理。
父親為人溫文爾雅,雖然替人打工,也不卑不亢,這個傳統留到了我,也是同樣的態度,我們一家是文人,也有文人的骨氣。
自從有記憶就知道了這家叫大華的戲院,當年發行電影是由邵氏負責的,父親當了這家戲院的經理。我家就在戲院的三樓,一走出來便看到銀幕,真是從早看電影看到晚。
戲院是在一九二七年由檳城富商余東旋1877~1941所建,余東旋是廣東人,小時就培養起對粵劇的興趣,傳說中是他的第三個妻子也會唱粵劇,有次到牛車水去聽,遭人所拒,回家後向先生告狀,余東旋一氣之下在新加坡的牛水車買了地皮,興建自己的戲院,叫「天演大舞台」,請了當時的英國著名建築家士旺和麥肯林設計。
戲院外表最顯眼的是那五幅粵劇人物的造型,千方百計不惜工本地在大陸燒成牆磚,一塊塊嵌起來,至今還企立着,因為是瓷磚關係,不會生苔,也當然不脫色,歷久如新,各位有機會到新加坡不妨順道看看這座歷史性的建築物。
一九四一年我在戲院的家中出生,根據我姐姐蔡亮記憶,是由接生婦在家裏接生的。到了我三歲時,有了記憶,是每天走出來看電影。當年新加坡已被日本佔領,放映的都是日本片子,有一部我記得最清楚,是李香蘭主演的《萬世流芳》1943,主題曲的《賣糖歌》聽得如雷貫耳。
從三樓的家走出來,就是一個包廂式的露台,有個石頭做的欄杆,相當廣闊,我不停地看電影,眼睏了就在那大欄杆睡覺,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樓下去,好在命大,沒有發生過災難。
因太平洋戰爭已到了尾聲,前來轟炸的飛機變成是英國人的,大華戲院目標大,避免不了,一顆大炸彈就扔到了我們的屋頂,好在沒有爆炸,但卡住了也不是辦法,反而是日本兵前來拆除,兵工隊小心翼翼地把炸彈鋸開,取出撞針,臨搬走時,家父請求把炸彈的尾部那翼子留下,又到玻璃匠處做了一塊大型的玻璃鏡面,鋪在炸彈翼上,當成了我家的飯桌。
三歲生日那天,英國空軍又來炸了,媽媽剛好煮了一碗麵給我吃,潮州人的傳統,生日要吃甜湯煮的麵,麵上還有一顆雞蛋,烚熟後剝殼,後用一張寫揮春的紅紙把雞蛋染紅。
我先把蛋白吃了,警報聲大作,大家都逃到防空洞去避難,看着那顆留到最後才吃的蛋黃,實在誘人,我忍不住一口吞下,卡住喉嚨,如果不是爸爸從我背後大力拍打吐出來,便會被蛋黃嗆死,從此一生人只愛吃蛋白,絕對不去沾蛋黃。
在日本軍統治下的新加坡,六先生也被抓了進黑牢,他有一次告訴我:「人沒有想像中那麼脆弱,我被關進牢中七天七日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但是死不了。」我聽了半信半疑,但也不好意思去質問真假。
日本人知道要安定民心,總得給人民娛樂,就把六先生放了出來,戲院由他去管理,大家會奇怪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還有人有心情去看電影?說的奇怪,人心越是恐慌越是往戲院中鑽。
六先生生了二男二女,二女兒和我同月同日誕生,她還記得小時的教育沒有學校讀,她們一家都由我媽媽當家庭老師教導。在戰亂時期女性最強,邵家已不發薪水,媽媽負責起全家的收入,到郊外採了許多野生芒果,是又硬又酸的,把這些芒果用糖醋浸了,切成一片片地在路邊叫賣,也賺了不少錢。
當年客人付的是日本政府發行的紙幣,記得背面印有一棵蕉樹,樹上生了一大串香蕉,人們都叫它為「香蕉紙」,紙張和印刷技術粗糙,很容易假,但也沒人去假。
因為我們家有收入,父母的許多朋友都來借債,日本人投降之前沒有人來還錢,一打敗了大家都揹着一大袋一大袋的香蕉紙來歸還。
媽媽看着那一大堆的香蕉紙哭笑不得,就拿來給我們當玩具,我們把一張鋪平,一張叠折,一連串地變成了一條條紙龍,亂踢一番,哈哈大笑。
新加坡光復後,爸爸繼續為邵氏打工,我們搬到一個叫「大世界」的遊樂園中,爸爸花了六十塊錢搭了一間木屋,稱之為「六十元居」。
「大世界」的原本概念來自上海,邵氏兄弟想家,但歸不得,就在新加坡買了一塊地,依照上海遊樂園的藍圖建起來,裏面先有電影院,接着是舞廳,然後有真人表演的舞台、商店等等。人們戰後都要娛樂,「大世界」生意滔滔,同樣地又建了「新世界」、「娛樂世界」等等。
家父當了「大世界」的經理,我就在那裏長大,戰後沒有學校,一群左派人士就在娛樂場之中組織,像打游擊一樣,這間戲院、那間舞廳中成立臨時教室,讓孩子們有地方上課,六先生很樂意借出這些場所。
最記得第一課上的是「咱們都是中國人」,這個「咱」字還是第一次認識的。六先生後來也提起此事,他建立學校的願望,也是從那時候種下種子。
邵氏片廠
2020/12/09在社交平台的網中看到一幅照片,真的可以用百感交集來形容,那是邵氏影城,通往這個東方好萊塢的夢工場主要建築。外牆像一個鉅星剝脫的化妝,如果邵逸夫先生看到了,也會像西洋人形容,在墳中也翻個身吧?
我從小因家族關係,已認識了邵先生,後來自然而然地跟隨着他,在他身邊最少也有三十多年。對於這個皇朝,我有講不完的故事,記得有一次和金庸先生在意大利旅行,乘着車子從意大利的維拉比亞納海邊一直走到羅馬。
在車上為了解悶,就聊起邵先生的事蹟,也不知不覺地談了好幾天,聽得查先生夫婦津津有味,我知道他們是不會告訴別人的,所以沒有保留,對外我就從不公開。
現在故事中的各個人物都走得七七八八,我自己的記憶也大不如前,是時候把記得的事寫下來了,而且不必有甚麼顧慮,反正都是真正發生過的,沒有添油加醬,事實到底是最有趣的報導。這段歷史要不留下來,也將永遠埋葬。
回到照片中的那座建築,在光輝的日子中大門的側邊路上,一直停泊着多架汽車,有邵逸夫先生的勞斯.萊斯,一向等着他隨時出入。再來的是小生們的跑車,各種型號,和女明星的賓士。另有多輛福士九人座小巴士,這是來往清水灣和市區的主要交通工具,在那七十年代非常流行,又便宜載人又多,只是缺少冷氣,也從來沒有聽人抱怨過。
門口是接待處,有位電話接線生守着,對着一排沙發讓來訪者等待,再爬上二樓就是邵逸夫先生的辦公室。他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我通常稱呼他六先生,不肯學別人叫他為六叔。非親非戚,何必諂媚?
六先生喜歡電影,他是真正地愛好,並不像鄒文懷先生,他只當電影是半業,平時可以不看就不看。六先生一有空就往他辦公室外的試片室裏鑽,他有一個專人為他放映的職員,名字叫阿邦,非常忠心,住在宿舍,隨傳隨到,二十四小時為六先生服務。
試片室外掛着一幅巨大的溥心畬的山水,沒有人懂得欣賞,也沒有人想偷,現在是價值連城的作品。
再爬到三樓,就是個餐廳了,當年影城中有兩個餐廳,一個在大廈的三樓,一個在攝影棚中,來客都是鼎鼎大名的演員和導演,如果能坐在其中,是個榮耀。
六先生在六十多七十歲時還是很健壯,又常練太極拳,他一口氣從大門爬到三樓,一點也不氣喘,也常笑那些出名的導演走不到兩三步路就要他們的老命,指的當然是張徹,他可以不動就不動,從影城中的宿舍到攝影棚常乘他那輛法國雪鐵龍轎車,連短距離的攝影棚和攝影棚之間也不肯走路,到了晚年他的腰已彎得不能直起來,實在是一個悲哀的狀態。
但從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完全不是那個樣子的,他當年還是「阿飛」,前額留着一束打着鈎的頭髮,時常用手去捲。張徹很注重儀態,身上衣服總是穿着同一個顏色系統,有時還把打火機放在桌子上,指着他的袖口袖子和打火機是同一牌子,同一設計的,這都是後話了。
我還沒有正式被調派到影城之前,只到過兩次,那是我從新加坡乘飛機來香港,再由香港坐郵輪到日本時,當年第一次走進邵氏大廈三樓的餐廳,簡直像劉姥姥到了大觀園,整個餐廳佈滿了各種歷史人物,時裝和古裝,當年對歷史的考據並不嚴格,不管是甚麼朝代,都叫古裝,之後的叫時裝,可笑得很。
只見嘴含着大雪茄的,就是導演了,導演有導演樣,戴着個巴雷帽,不含大雪茄形象就不行了,還好他們沒有把麥克風的傳聲筒拿在手裏,最典型的是岳楓導演,他咬着大雪茄咳嗽個不停。
大明星也來了,但不叫餐廳裏面的菜,她們有兩三個跟班的婆娘,拿着好幾個食格,一格格地把不同的菜肴拿出來請導演們吃。其他工作人員,包括茄喱啡,都不會來到這棟大廈主要的食堂,他們只能去攝影棚中那家。
我在日本半工讀,一下子就學會了製作,在那裏負責一切到日本來拍外景的工作,凡是有雪景的片子,都幫香港拍,所以認識了岳華和王羽。第二次來邵氏片廠時,他們兩個剛好都在拍戲,看到了我,堅持收工後請我吃飯,我左右為難,不知道和誰去好。大家都年輕,血氣方剛,爭執之下,就大打起來,也不像電影裏那麼拳來腳去,只是互毆,後來乾脆扭成一團,跌到溝渠裏面去,好在沒有記者在場,否則報導起來實在成為笑話,我寧願是兩個女明星為我吵架算了。
我這篇東西,扯東扯西地寫,也沒有拍照年份,也不分次序,自從出現了一個塔倫天奴之後,電影也可以亂剪,我的記載,也就是那麼想到甚麼寫甚麼,最後如果能輯成一本書,那就是大喜事了。
花花世界
2020/12/02
瘟疫期間,悶得發慌,鎖在家裏的日子,怎能過呢?一定得找些事來消解,才對得起自己。
很多朋友建議我在Patreon開一戶口,自言自語地發表言論,如果有人看,還可以分成呢。我當然也研究過,發現並不對我胃口。
如果做Podcast的話,我寧願在YouTube上做了,這是一條大道,看的人也最多,香港人對YouTube最有信心,一得閒就上去逛逛。
當然在內地的平台有更多的選擇,但得講國語,我始終長居香港,用粵語做Podcast應該更有親切感,和大家商討的結果,還是在YouTube做Podcast。至於怎麼照顧到聽不懂粵語的觀眾,我則會加上字幕。
叫甚麼呢?我也想了很久,最後決定用回我的店商名字《蔡瀾花花世界》,也代表了我不談政治的立場,只談風月,不講政治。
通常做一檔Podcast節目是不花本錢的,弄一個拍攝機或更簡單的iPhone,對着自己,就可以開始直播了,但看別人的,總覺得粗糙。開始的時候還是要精密一點,嚴謹一點的,所以先要來一隊攝影及燈光組,再加上後期的剪接與字幕組,一切花費不少,是否有錢賺不知道,但事實是先得被打三百大板,這也不要緊了。
做Podcast最主要的還是內容,講些甚麼有沒有人感到興趣?看不看得下去?才是關鍵。攝影和字幕的投資,我是不惜工本的。
自言自語總不是我的強項,我不是一個話多的人,有些人一開口就講個不停,內地人稱這類人物為「話勞」,我很佩服,但我做不了,還是找人對答較為流暢。
當然我有許多演藝圈的朋友可以找來做主持,但我不想勞煩別人,還是請了我生意上的拍檔劉絢強先生幫忙,要求他兩個女兒上陣,大女叫Shirley,小女兒叫Queenie,她們都是一直跟我旅行團到處去的,從小看到她們大,當成自己女兒了。
Shirley口齒伶俐,又很愛吃東西和喝酒,在吃喝方面很容易配合到我。Queenie很乖,話不是太多,一直喜歡烘焙,從小愛做麵包,非常出色。她做的餅乾好吃得不得了,有種椰子餅,更令人吃得上癮。
有了這兩人助陣,我做起這檔Podcast節目時輕鬆得許多,但所花的時間和精神是不少的,我總相信這是應該投入的,連這一點也不肯下工夫,怎能做得好?
許多人想做這個,想做那個,說得老半天甚麼都沒有做得出來,我不是這種人。我說做,就做出來,所以《蔡瀾花花世界》這檔節目就產生了,在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首播。
最先拍的是我新結交的意大利朋友Giandomenico Caprioli的意大利雜貨店,就開在分域碼頭。你想到的甚麼意大利食材都可以在這裏找到,非常齊全。
節目出街之後,我打電話問生意有沒有幫助,回答客人增加很多,多人回應道我介紹得不錯,總之有反應是好過沒有反應。
本來,我的原意是一個星期在YouTube中播出一集,看視頻的人不喜歡看太長的,只要剪成十分鐘左右就夠了,否則太長也會在手機上看得昏頭昏腦。
但是,以我本人觀察,看了一集之後,再要等一個星期才有第二集,是不夠喉的,是不滿足的,我即刻吩咐我的製作團隊,不要等多七天,馬上連續在第二天的星期六再做多一集。
第二集的內容是把所有在超市買的東西放在桌上,當成野餐,把醃製的肥豬肉切成薄片,再配上清新的意大利蜜瓜吃,加上聖丁紐爾的火腿,以及用豬頭肉壓成的薄片,還有種種的食物,同時也介紹了妹妹Queenie出現,嘗試她做的麵包。
第三集連續追擊,把買回來的八爪魚煎一煎,將地中海紅蝦做成意粉,淋上紅蝦油和紅蝦粉,是美味的一餐。這時候,拿手的甜品出現,妹妹做的杏仁薄脆出色,白色朱古力撻,貓山王榴槤甜品等,都非常出色。
果然三集同時推出是有它的震撼,可是壓力續繼來了,每星期三集的話,後期的製作是困難的,但怎麼困難也要頂硬上。
下一個禮拜我們推出了上海菜系列,也是一連三集,YouTube上有所看人數的統計,但我是不看的,看來做甚麼?只要做得精彩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像我在微博上做的,看的人叫粉絲,我的粉絲是一個一個努力賺回來的,至到目前為止有一千多萬。我不能期待YouTube上有這種成就,既然開始了,就把頭埋進去,每次努力地做好它。
對得起自己,就是了。
《若不關懷》
2020/11/25
最近又重聽了一首叫《若不關懷 If I Didn’t Care》的歌。乖乖不得了,這一來我又重新着迷,聽完又聽。在Spotify和YouTube上找到所有人唱的,所有樂器演奏的,百聽不厭。這首曲子緊緊地抓住我不放,繞樑三日回味無窮。我睡覺和醒來,腦中完全是《If I Didn’t Care》。
從前有一首叫《哀傷的星期天 Gloomy Sunday》的,聽完大家都自殺去,這一首不止令人陶醉,也可以讓聽者懷念初戀的情人,以及想起種種的別離,卻不太過悲傷,只是懶洋洋,無可奈何,非常地優雅。
此曲為Jack Lawrence所作,他本來受聘於好萊塢製片公司,專為電影作曲,這首只是他的閒情之作,無心插柳地給了唱片公司試試看是否可以發表,Decca轉給了一隊叫《墨跡The Ink Spots》的四人組合,當年他們唱甚麼也不紅,一樣抱着嘗試的心態錄下這張唱片,時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想不到一炮而紅,聽過的人都不會忘記。這隊黑人組合,影響了後來的The Platters,兩者比較之下,你就知道墨跡高出許多。
唱片一出爐,著名的歌手和樂團紛紛搶着錄唱片,連鼎鼎大名的Bing Crosby和Frank Sinatra也照唱,最著名的樂隊Count Basie, Louis Armstrong也不肯放過。歌詞為:
If I didn’t care,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If I didn’t care, would I feel this way ?
If this isn’t love then why do I thrill ?
And what makes my head go’round and’round while my heart stands still
If I did’t care, would it be the same ?
Would my ev’ry prayer begin and end with just your name ?
And would I be sure that this is love beyond compare ?
Would all this be true if I didn’t care for you
此處加上旁白:
If I didn’t care, Honey child,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If I didn’t care, would I feel this way ?
Darlin’ if this isn’t love, then why do I thrill so much ?
And what is it that makes my head go’round and’round while my heart just stands still so much ?
此處回到歌詞:
If I didn’t care, would it be the same ?
Would my ev’ry prayer begin and end with just your name ?
And would I be sure that this is love beyond compare ?
Would all this be true, if I didn’t care for you
對於不懂英文的讀者,對不起,我試中譯過幾次,都詞不達意,有些歌,只能以原文唱。
《墨跡》唱完這首歌後平步青雲,接着的歌也炙膾人口,有《我再不微笑了 I’ll Never Smile Again》、《撒謊是罪過的 It’s A Sin To Tell A Lie》、《我不再點燃世界 I Don’t Want To Set The World On Fire》,以一貫的作風,歌唱到一半加入旁白。
後來的許多電影製作人也為此曲着迷,不斷地在各種形式之下用完再用,《月黑高飛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一開始就出現。《狂牛 Raging Bull》1980,《娛樂大亨 The Aviator》2004等名片,一有四五十年代的背景必唱此曲,我們又怎麼會漏掉愛好爵士的活地亞倫呢?在他的《歲月流聲 Radio Days》1987出現。
最可惜的是Ridley Scott的《銀翼殺手 Blade Runner》1982本來是機器人和男主角作愛那場戲想用的,但是作曲家已把版權賣了給披頭士的Paul McCartney,要了個天價,只有改用Vangelis的 《One More Kiss, Dear》遜色得多。
為此曲着迷的歌手無數,Connie Francis, Brenda Lee, Bobby Vinton等等,都可以找來聽聽,有些以慢調唱,有些輕快地唱。最值得看的是《Miss Pettigrew Lives For A Day》2008,女主角本來為了金錢要與窮鬼鋼琴師分開,但他彈了這首歌,兩人合唱的場面深入人心,是拍來向此首曲致敬的,可以在網上看到片段。
別以為好東西只有老頭子會欣賞,現代愛好音樂的年輕人不少,他們一聽到此曲也即刻着迷,被大陸人叫為「甜茶」的Timothée Chalamet也對着鏡頭唱,雖然他的歌聲不像外貌那麼吸引人。
我最喜歡的還是Allison Young,她自己彈鋼琴自己唱,有股很清新的氣質,各位可以找來看看,必定着迷。
聽覺享受
2020/11/18
我天生對味覺十分敏感,一嚐到食物,即能分辨出有無防腐劑來,上天是公平的,令人得到一些,失去一些,所以在聽覺上我是差過很多人。像一些朋友買了精密的音響設備,能聽出交響樂中的每一個音符,這種享受倒是我缺少的。
看書是從小培育的習慣,吃東西自然產生味覺的分辨,至於聽覺,我沒有受過甚麼訓練,也不追求,對音樂的認識,最記得的是那個麗的呼聲的木盒子,每早一開始就傳出《溜冰圓舞曲》原名《Les Patineurs》,英譯《The Skater’s Waltz》,就算自己不願意,也會入腦,至今隨口便能哼出來。
音樂對一個少年的成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因為愛電影,每看到一部,它們的主題曲或背景音樂便能牢牢地記於心頭,有些也不是當年的,像一部叫《翠堤春曉 The Great Waltz》的,是我出生之前的一九三八年拍攝的,後來重映,才記得讓人陶醉不已的《維也納森林的故事》和《藍色多瑙河》,以及為此片創作的《當我們年輕時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除了電影,走在街頭也能聽到的流行曲《Seven Lonely Days》也深深地烙印在我腦海中,美國流行曲最能代表一個年代,聽一個人哼出些甚麼歌曲,就知道這個人有多少歲了,所以看傳記,流行曲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絕對不能忽視。
在瘟疫期間,網友要我介紹我喜歡的音樂和歌曲,我就憑着記憶,一數就有一百首以上的歌曲來。有些是馬上記得,有些拜賜於當今的搜索機器Spotify,它有一個能叫Daily Mix,就是將你選出的歌曲做一統計,幫你組織一些年代與背景相關的曲子來,我可以從中挖掘一些已經埋葬了的記憶,說出當年當時喜歡唱的歌,以及讓這些曲子流行的歌手。
最先出現了Bobby Vee,他唱了《More Than I Can Say》,接着當然有膾炙人口的Pat Boone,那年代的人誰會忘記《Love Letters in The Sand》呢?還有Cliff Richard的《Summer Holiday》和《The Young Ones》,當然也忘不了Bobby Vinton唱的《Sealed With A Kiss》,因為那是當年我第一次來香港聽到的流行曲。
「你談的都是老餅的歌,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小朋友們抗議。
我會回答:「現在是我在寫文章,你不喜歡別看,當你自己能夠寫時,再去談Billie Eilish、Selena Gomez、Ariana Grande及Sada Baby吧。
但是有些網友,回聽我介紹的那些老得掉牙的歌,也開始欣賞起來,令大家感到興趣的是,能聽得清楚歌手唱的是甚麼。
這些老餅,都必要經過嚴格的丹田訓練,珠圓玉潤地唱出每一個字來,不像當今的只要能「喊」就是。聽歌嘛,最低要求應該是聽得懂嘛。
從聽歌學習英文,是件快樂的事,我的英語基礎也是拜賜聽流行曲得來,而唱得最清楚莫不過Nat King Cole了,一旦喜歡上他的歌,又是一個歡樂的天地。
與他同時的還有一個叫Johnny Mathis的,不但歌詞聽得懂,而且能聽出絲綢一般的味道來,其他的,像Matt Monro、Andy Williams、Tony Bennett等等,都沾上一點。
你可以說這些人唱的都是抒情的慢歌,所以較為易聽,但是你去試試,Bill Haley And His Comets、Little Richard、Chuck Berry、Buddy Holly的搖滾吧,當然也可以聽得出每一句歌詞來。
也別看輕貓王Elvis Presley,他的情歌是那麼清清楚楚,尤其是後期經宗教洗禮後唱的更是動人,民謠更是好聽,所以我選了他唱的Danny Boy介紹給大家。
除了歌唱,音樂帶給我享受莫過於爵士了,我的接觸也是拜賜於電影看法國片《通往絞刑架的電梯Ascenseur pour l’échafaud》1958,配樂用了Miles Davis的爵士,他的演奏,被公認為天下最寂寞的樂器聲,一聽即知悲傷是甚麼一回事,馬上哭泣。
打開了爵士的天地之後,接着來的是《Take Five》、《Harlem Nocturne》和Louis Armstrong的《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再下來欣賞的是怨曲Blues了。
這可得女人來唱,不管她們的樣子美醜,身材多肥,依然能唱出了李清照式的各種哀怨來。代表的有Ella Fitzgerald,她的每一首歌都好聽。誰能忘記Julie London呢?她的《Cry Me A River》一直圍繞着聽者不放,還有數不清的Sarah Vaughan、Eva Cassidy、Billie Holiday、Laura Fygi、Norah Jones、Diana Krall……
順帶一提,Spotify除了歌名歌手名之外,往上一掃,還能有歌詞出現,聽現代歌手伊伊呀呀的詞,也能懂得了。
大哥
2020/11/11
小時,一直和大哥蔡丹沒有甚麼兄弟緣份,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從來記不得他有帶我去抓魚抓鳥的記憶,兩人並不親近。
爸爸年紀大了,在邵氏中文部經理的職位就很自然地傳給了他,從公司回來,他必先路經老家,為爸爸帶來當天的晚報和一些海外雜誌,從不間斷。
長大後我開始負責擔當製片的任務,也帶過何俐俐、林沖等明星回新加坡拍外景,當年甚麼都省,沒有外景經理這個職位,一切拍攝的雜務,也由大哥承擔起來。我當時年輕氣盛,工作一沒有安排好即刻向大哥大發脾氣,他沒有做過電影製作的崗位,當然有出錯之處,我不諒解,現在想起來,十分後悔,但當然,後悔是來不及的。
我不知道為甚麼我們兩人合不來。有件事,當今想起,也許是起因之一。我們小時候在一個叫「大世界」的遊樂場中,來了一對父女的流浪藝人,父親表演吐金魚,女兒擔任助手。她的名字叫董雲霞,是位北方姑娘,對我很好,有次聽到她和大哥去拍拖,其實也不是甚麼談戀愛,一起去吃個飯,看場電影之類,但對還只有十一二歲的我,是場重大的打擊,從此對大哥更不瞅不睬。
長大後,更沒甚麼可以溝通的,大哥愛做生意,喜歡跑馬,都是我覺得最乏味的事,我們兩人雖然沒真正吵過架,但不親就是不親。
大哥自小就對我沒甚麼意見,他好像一隻不知道仇恨的動物,從不記仇,我偶而回新加坡探親,他也常帶我去嘗街邊小食,我們兄弟的共同點,大概只為吃吃喝喝這回事了,其他甚麼共同話題都沒有。
第一次令我對大哥的印象改觀的是,有回爸爸生病,不便於行,大哥不但每天照顧,還帶爸爸去看醫生,不是只用汽車接送,而是親自揹着老人家去看醫生的。
當年爸爸應該有六十多歲,大哥已有三十多,那麼大的一個成人,還肯親自揹老人家走出走進,在從前的社會也許常見,但在繁華的現代,是少有的。看到了,才知道甚麼叫感動。
從那時候起,我們聊天的機會多了,他常來香港,是負責和香港片商打交道,買他們製作的電影去新馬放映,這是爸爸以前的工作,後來都由他打理了。
片商們應酬發行商人,在電影界是理所當然的事,大哥常與他們去吃飯,偶而也帶上了我,雖然我並不喜對此類應酬,但也陪着他。
每次大吃大喝之後,都要到醫院去洗血,這時大哥已患上相當嚴重的糖尿病。但大哥的飲食習慣也不因為毛病而減少,他還是盡量地吃,盡量地喝,吃喝完畢又是洗血去,對他那種嘻嘻哈哈的個性,並不覺得是一件苦事。
多年的暴食暴飲,終於還是吃出毛病來,聽到大哥進了醫院,我專程地回新加坡一趟去看望,見他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問道:「有沒有帶新書來?」
原來,從小不喜看書的他,到了後來,最愛看我的小品文,我一有新書必第一個送給他。
我點點頭,從和尚袋中拿出最新出版的一本,交給他時看到他的喜悅,我也欣慰。但欣慰之餘,才發覺到新書的名叫《花開花落》,好像預兆並不吉祥,這本書本來是紀念爸爸的,說他子女長成,孫女孫兒又是一群,人生總是那麼循環。
書交了給他後非常之後悔自己的粗心,但一切已太遲,他閱讀完後,含笑而終。
大哥在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一往生,才六十五歲,在這年代,大哥是走得太早,靈牌放在媽媽任職校長的「南安善堂」,和爸媽一起,我們每次拜祭父母時當然也燒一炷香給他。
大嫂知道大哥怕熱,在善堂另一處有冷氣的房間替他買了一個靈位,爸媽的也在旁邊。
大哥生有一男一女,兒子叫蔡寧,女兒叫蔡芸,蔡寧樣子也長得和大哥越來越像,尤其在走路時翹起了屁股,他讀的是電腦,但嚮往我們一家人的電影工作。他在美國長居,後來也加入好萊塢的華納公司,負責了電腦製作工作,對於電影的修復,他更是專家,曾經告訴我說他本來以為和電影無關的,但也當了第三代電影人,有點自豪。我非常喜歡這位姪兒。
女兒蔡芸在日本最榮譽的慶應大學畢業,事業上本來可以一路青雲,因為日本大學有照顧後輩的傳統,但她還是選擇了家庭。偶而也喜歡寫作,在《蔡瀾家族II》那本書上有數篇她的文章。
大哥在天上看到,也感歡慰。
我們兄弟,當今的情感應該是最融洽的時候,在夢中,常和大哥聊天聊到天明。
流浮山
2020/11/04
海鮮的話,如果說是到西貢或鯉魚門去找,食魚專家們如倪匡兄聽到了一定嗤之以鼻,要是說去流浮山,他們才點點頭。
很久沒來流浮山了,記得最初前往實在是山長水遠,從市中心出發,非花上一小時以上的車程不可,但為了生猛的魚蝦還是照去,後來路打通方便得多,不過也至少要四、五十分才能到達,所以不是一個常去的地方,如果不是招待遠方好友,不會到流浮山。
最近,認識了一位新朋友,對食材非常敬重,也肯到處品嚐,和他雖然不是十分稔熟,也答應帶他到流浮山走走,之前告訴他,千萬別穿甚麼好皮鞋,有些地方還是涉水而行的。
在迴轉處下車後,我們經過那窄長的巷子,兩邊都是食材檔口,就可以走到碼頭。星期天,遊客也還不少,都是本地人專程而來。
大家買最多的是乾蠔,流浮山從前以產蠔著名,盡頭處可以看到由蠔殼堆積的山丘,實在厲害。當今環境被破壞,生蠔已經沒人吃了,但乾蠔還是很受歡迎,種種吃法,變化無窮。
我帶友人先到達小巷左側的商店,海邊街八號的「汝記蠔油公司」去。蠔油已是常用的調味品,許多網上的做菜師傅,包括潮州人山哥,也常加一大匙蠔油,因為大家對味精敏感,不太敢用,但大加蠔油則沒人反對,其實也放了大量味精。
我家用的過半是日本產的「頂天」,用的蠔汁特別多,一般的生蠔極少,有些次貨還以青口代替,也沒甚麼人吃得出來,但「頂天蠔油」也帶了很重的防腐劑味道。
「汝記」的產品也分等級,買最貴的約七十塊港幣一瓶的好了,調味品不能當飯吃,貴一點也無所謂。
當今因疫情,餐廳也不開早市,所以沒約友人一早來到,從前我都喜歡清晨來流浮山,在碼頭上看到內地來的漁船排成一排湧來,非常壯觀。
這時就可以選最新鮮的魚蝦蟹了,如果遲去,只有在海產店中採購,賣的和西貢鯉魚門完全不同,沒有甚麼阿拉斯加螃蟹之一類的舶來海鮮,這兩個地方只有墨魚是本地的。
最佳選擇當然是黃腳鱲,這種最香最鮮美的魚,賣的價錢也不貴,記得最愜意的一次是和倪匡兄來吃,見店裏有,只說有多少尾就買多少尾,結果買了八條魚,都是比手掌大一點的尺寸,最佳狀態即蒸出來。
倪匡兄一見大喜,我們看他那種歡悅的表現,自己都不捨得吃,我的一尾留給他,其他友人也留給他,結果他老兄一人幹掉了八條魚。
拿去做的地方當然是「海灣酒家」了,這家人已光顧了三四十年,主掌的是大家姐,我們都叫她做「肥妹姐」,樣子數十年不變,她帶着兩個弟弟每天在店中守着,你們去找她好了,想不出要吃些甚麼的話她都會代你出主意。
這家人最厲害的當然是蒸魚,大小不同類型的魚,放在同一蒸籠中,他們也會一口氣為你蒸出來,生熟度完全是靠擺在不同的位置,這是驚人的手藝。
說到蒸魚,香港敢稱天下第一了,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地方比香港人蒸得更拿手,這句話是在各地吃過之後的比較,全無虛言。
帶這位友人來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吃過他的家廚做出來的,可用廣東人一句老話形容,叫甩皮甩骨,好好一條魚就那麼浪費了,從前和倪匡兄到餐廳去,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總會發脾氣,當今大家都老了,笑笑算數,說是自己要求過高,不關廚子事。
我們坐的是靠近廚房的餐桌,一般的魚聞不到,但是黃腳鱲的話,真的可以說是香味陣陣傳來。
各種魚吃過之後,我都把碟中剩下的魚汁連薑葱一齊留在一小碗中備用。
接着吃白灼蝦,啊!這種佳餚從前宴客時必點,後來跟着產量少,基圍蝦又佔了食桌,真正本地產的九蝦和麻蝦都不見了,今天在當地買的兩斤九蝦,白灼了吃,像嚐到沙糖那麼甜美,吃剩的蝦,剝了殼後放進飯中炒。
「海灣」有兩道名菜,一是蝦膏炒飯,一是海龍皇湯,前者不管你有多飽,也能連吞三碗。友人懂得欣賞,把魚汁淋在炒飯上,見他吃得津津有味,我覺得這回帶他老遠來到也是值得。
海龍皇湯則是把龍蝦、瀨尿蝦、雜魚、沙蜆一塊煮出來。看季節,秋天下白菜仔,冬天則下大芥菜和豆腐,絕對不要貪心,有多少人喝煮多少碗湯,燒出來的,也是天下美味之一。
甚麼地方旅行不了,去流浮山走走吧,別的不說,單單是這兩道菜,已值此行。
海灣地址電話:流浮山正大街四十四號,電話:2472 1011,去時最好先打給他們,有甚麼想吃的海鮮也可以請肥妹姐留給你。
大姐
2020/10/28
拜賜社交平台,大姐蔡亮和我的接觸已越來越繁密,這是數十年來從未有的事。
小時,我們三兄弟都受大姐的教導,媽媽事業心重,一家人的功課就由大姐頂上,所有不懂得的都問她,好過任何百科全書。
我們都受父母的影響,大姐理所當然地走上教育一途,媽媽當校長,她也當了校長,而且是新加坡最權威的女校南洋中學,不是易事。
認識一些女生,在星馬或在大陸,都是她的學生,一提起校長,大家都有敬畏之心,她的嚴格訓練,令到她們牢牢記於心,說起大姐,她們和我皆感到驕傲。
也許是潮州人的傳統,女兒出嫁後多顧夫家,自己的親人反而沒那麼親近,我們的媽媽也是,大姐也是,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逐漸疏遠。
離開家後,父親與我的通信還是不絕,姐弟們就不大聯絡了。當然在爸媽生日時大伙還是相聚,在老人家過世後,我們每逢忌期,都一齊在墓前參拜焚香,事後兒女們包括他們的下一代,到餐廳去大吃一頓,付錢的還是媽媽,她精於經營,過世後還留下一大筆錢當公款,子女們的聚餐,由她一直負責下去。
本來一年總會見兩次面,父母忌期各一回,後來大家逐漸事忙,清明也變成集合起來,一次過上香,這麼多年來沒變。
每次見大姐,都那麼充滿精力,除了頭上多些白髮,活躍如常,退休後照上跳舞班,家裏當然打理一切,姐夫的病痛全部包辦,兩個兒子做律師,還當小孩們照顧,也包括孫子孫女。
年紀一大,病痛當然隨着來,膝頭有毛病也大膽地開刀,看着她拿着拐杖一跛一跛辛苦走路,也看着她復原,繼續跳舞去。
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姐夫的去世,但她並沒有氣餒,一直要想做些甚麼來解脫這段人生傷痛,是我報答她親情的時候了。
我引導她寫《心經》,在文聯莊買了所有工具寄到新加坡給她,從墨到紙張,應有盡有,大姐開始每天寫一篇,然後在微信上傳給我,起初歪歪斜斜,到每行工整筆直,那段時間從不間斷。
到了百篇之後,她問我如何處置,我回答說可以燃燒後回向,但她選擇留下,每天繼續寫,寫得紙用完,我跟着寄,毛筆和墨汁用完,我繼續寄。
她寫的心經,應該已是厚厚地一大叠了。筆劃工整後,我還寄上歷史上的每位名家所寫的心經,希望她能在讀帖後作字形的變化。
所傳來的,最初我只略作鼓勵性地說好,但逐漸嚴格地指出每一行的開頭和結尾的錯處,這都是按照馮康侯老師的教導,說字與字之間要有大小,行與行之間要互相地謙讓,這麼一來才能發生情感。
有時毛病出在結尾時不整齊,總是留着礙眼的空位,我指出後也改不了,不客氣地講了多次,她才了解有些字怎麼放大,有些字如何縮小,結尾時才能拉齊。
除了心經,大姐又開始作畫,喜歡畫花卉,這方面她比書法進步得快,是有天份的。練習不久,已像模像樣,她的學生來求,也可以畫給她們,簽名時得有一個圖章,我本來自己可以刻給她的,但近來眼睛已沒以前好,恐怕刻得不像樣。
求師兄禤紹燦給她來一個最好,但大姐還沒有達到那個階段,還是求陳佩雁吧,她是禤紹燦師兄的得意門徒,作品沒有一丁丁的俗氣,是我喜歡的。我最近的幾方印都是出自她手筆。無所報答,唯有用書法和她交換,每次都問她想寫甚麼就寫甚麼給她,也算是公平交易。
完成後寄給大姐,她也說很喜歡,等她的字和畫有進一步的階段時,再請禤師兄動手,到時我也會盡量拿起刻刀,為她來一方。
我好珍惜與大姐溝通的這段日子,想不到大家都老了,才產生這麼一段姐弟情。
之前,我們一家人合作了一套《蔡瀾家族》的書,第一本由天地出版,編輯和印刷上都下功力,得到當年的出版獎,第二本《蔡瀾家族Ⅱ》也隨着面市,文字之中加了我大哥的女兒蔡芸的文章,第三代人,也有我父親的遺傳。第三本的文章和照片都由大姐準備好,可以付之印刷,我懶於動筆,說不用我寫了,但大姐反對,要我加一份才行,所以有這一篇文章的產生,這本書中,會加上大姐孫女們的文字,這是第四代了。
本來還想寫父母及大哥的,但一想到就有點悲哀,我的眼淚已經流完,再也擠不出了。
搜索些甚麼?
2020/10/21
有很多網友問我,你用甚麼iPad?常用的App有那幾種?
回答你的問題:我的蘋果iPad一向是最新最快的,沒去記得是甚麼型號,總之是容量最大的iPad Pro,有甚麼更新的一出,我一定換,我覺得如果能用錢來買每天必用的工具,是很便宜的事,舊機很多部,都送友人,他們不追新款的,並不介意。
一開機,介面是一尊如來佛像,旁邊的備前燒花瓶中,有怒放的粉紅色牡丹花,這是在家中拍的,我很喜歡佛像是似笑非笑的表情,而牡丹花,如果有荷蘭運來的必買。花期雖然不長,只可擺三四天,但我見到就開心。
介面的第一個icon是相機,我已習慣常用iPad來拍照,如果外出,則用iPhone,反正幾乎同時就傳到。
旁邊的是相片檔案,全部已經拍了三萬一千多張,整理及刪除起來是一大工程,所以盡量不去碰,讓它不斷地增加好了。
照片上從前有許多是食物的,當今已不大去拍了,貓的照片反而是最多,每種形態及表情都留下,有一天學用毛筆畫貓時,可以當成參考資料。
書法的照片也無數,我一看到新的字形必定錄下。啊,原來這個字可以這麼寫的!好的句子也當然拍了,練書法時可以寫寫,最近錄的有很多書齋的名字,像「抱膝吟齋」,「竹軒」、「半日閑齋」、「望雲小舍」等等,自己是不用了,如果有人喜歡可讓給他們。
icon上還有一個「草書書法字典」,最近草書字帖看得最多,自己寫字運用得上,也不能一一記得清楚,大家以為草書糊裏糊塗,但馮老師教導的是,草書最為嚴謹,一筆一劃都應該有出處,一錯了就變別字,所以我寫完草書後一定查一查,免得鬧笑話。
時鐘的icon也常用,我最為守時,每天要看很多個鐘,壁上有太陽能兼電波指示的掛鐘,一分一秒從無差錯,手上的錶也有此等功能,用上了,其他鐘錶都覺得靠不住,尤其是那種幾萬幾十萬的名貴機械手錶。
iPad上的這個時鐘功能,還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時間,打電話給人家先看看,才不會三更半夜擾人清夢。
再下來就是各個社交平台的了,「微博」我當然每天有無時不刻地更新,「微信」也相同,Instagram戶口就交給同事去管理了,不然太花功夫了。
Facebook也每天會看,我一發訊息就同時在「微博」、「微信」、「臉書」這三個媒界上,Facebook我經營得又慢又少,網友看的也不多,不過可以聯絡上一些失去的朋友,真感謝它。近來香港的網友增加不少,又有許多日本和星馬的,所以會不時地更新。
接着下來便是娛樂了,串流平台Netflix前些時候看得最多,但近來有太雜的傾向,不過我還是會不停地去發掘新節目。看最多的反而是亞馬遜的Prime Video,它的製作水準最高,自從看了他們製作的《Mozart in the Jungle》之後,更佩服得五體投地,變成這平台的頭號粉絲,幾乎將他們所有節目都看了。
「Now隨身睇」也常看,原因是它有一個付款才看得到的電影台,一有新作我當然不會放過,錢多少我也不在乎,我一向認為只要給錢就能得的歡樂,多少錢都是值得的,只嫌節目不夠多罷了。
其他的節目台像HBO GO的icon也在頁面上,這個台亦相當夠水準。至於雷聲大而雨點小的是Apple TV,除了《The Morning Show》之外就沒甚麼好看的,他們錢不是沒有的,只是眼光太淺,當今的總裁也沒甚麼光輝,如果Jobs還在,絕對不會讓他的招牌淪落到目前的地步。
至於Disney串流台,我已沒甚麼興趣,在其他地方看了他們的新作《花木蘭》,更失去信心。
其他的icon多是字典,《康熙字典》我常查,《書法字庫》少不了,《漢語詞典》可以勉強應付單字,《中文字典》、《中日日中辭典》、《日華華日辭典》、《英漢雙解詞典》、《翻譯全能王》等等都有時翻翻。
但用得最多的是「Google」了,中英英中翻譯它比所有的字典還要強,詩詞句子的出處也要靠它,一對節目有好奇,或在電影上看到製作者和演員,我都會上Google查,它滿足了我一部份的好奇心,這搜索機器實是偉大,一切知識都存入,我已是沒有它不行。它也有聲音搜索的功能,許多朋友都用口指示,但我到現在還用不慣。
同類的「百度」令我非常失望,所有的資料都不齊全或貨不對辦,為甚麼連中文的百科全書都做不好?應該打屁股。
學問是每天做了,有時會覺得悶,那麼只好靠「瘋麻將16張」這個icon去解解悶。在網上打麻將打得多了,和朋友開枱時常贏,覺得三人陪你,還要收他們的錢,有點不好意思。
從雙耳流出來
2020/10/14
困在家裏,甚麼地方都到不了,就算最近的澳門,去一下隔離十四天,回來又要十四天,白白地浪費將近一個月,值得嗎?
想去的國家太多了,既然出不了門,唯有作夢時走一走,算是名副其實的夢遊了。
BBC有個節目,所到之處都是大家熟悉的,但全部是一般旅客不知道的地方,剛好我都住過,看起來十分親切。
前後介紹過巴塞隆拿,這是我二十多年前拍《快餐車》時住過一年的都市,後來也經過三四次,但遊客太多,又時有吉普賽青少年搶劫事件發生,已失去了興趣,不過怎麼也好,等可以旅行時也一定要重遊,最好得到二○二六年聖家堂完成時看看,這是多年來的心願。
高地的建築在一八八二年開始動工,一直沒有停過,我去時一切還沒有上過顏色,遊客對它也不太注意,我就住在附近,一有空都把頭鑽進去研究,對它的一草一木都感興趣。
當年還結識了一個年輕的雕刻家叫Etsuro Sotoo,每天辛辛苦苦地刻石,他說只要能為教堂獻上一分力量,就是一生最大的滿足。
巴塞隆拿冬天冷起來也相當厲害,我看他衣服單薄,凍得全身發抖,在我拍完戲離開時把所有禦寒的衣着都送了給他,當今他已成了名人,不知會不會記得?教堂完成時他人一定在,也想找他坐下來聊聊天。
另外到過阿姆斯特丹,我雖然沒有長期住過,但每年一有機會就去拜訪丁雄泉先生,在他的畫室中向他學上色彩的運用,在他的廚房中包葱油包子吃,度過很幸福的懶洋洋的下午。
丁先生最喜歡的一棵大樹就他家附近,我們常散步去看它,他說:「這麼一棵樹,養活了幾百萬塊的葉子,你不覺得自然的偉大嗎?」
丁先生逝世後,我沒有理由再去阿姆斯特丹,但這棵大樹,總希望有一天再去看看。
近來在夢中也常見前南斯拉夫的首都,當今國家名稱已改成克羅地亞,但城市依舊,在夢中出現的,是從前住的旅館中走出來的那條街道,走呀走呀,經過街角的一個小聖母像,大家都在那裏點一枝蠟燭,如果再去,也一定會去點一枝。
當然也不會忘記那邊的羊肉,在野外架上個鐵架,鐵架兩頭裝有風車。把整隻羊架上,下面燃燒稻草,風一吹來就旋轉着羊,讓它慢慢地烤,熟後,拿到廚房亂斬,一手抓羊,一手抓一個洋葱,撒上鹽,就那麼一口口吃,其他甚麼調味品都不加,是我一生人吃過最好的羊肉。
最近有位好心的網友,把我以前拍過的旅遊節目都放在網中,其中有我在法國鄉下吃的櫻桃,那是一串串,紫色的果實,紫得很深,近乎全黑,但那是天下最甜的,如果能夠再去一趟,也會去嘗嘗。
新朋友之中,有位Gianni Caprioli,他經營的餐廳GIA和意大利食品店也是我最喜歡去的,有機會去意大利的話和他結伴,他會去拜訪他入貨的商家,一定吃到好東西。
有時候,舊朋友反而沒有再見的衝動,大家都老了,有點氣餒,見到的你可憐我,我同情你,不知道要說些甚麼才好,但話這麼說,還是想見的,剛剛接到韓國徒弟阿里巴巴的問候,我當然想和他一起去吃醬油蟹、烤鰻魚和所有我喜愛的韓國老味道。
還夢到吃雪糕,我這個雪糕癡已學會自己做了,日本的北海道牛奶做的軟雪糕可以吃到拉肚子為止,意大利的冰淇淋也百食不厭,他們說要原汁原味,原味的話,當然是甜,甜死人也,才夠味,我一點也不怕,怕的是清淡到淡出鳥來的雪糕,不如不吃。
巴黎的Berthillon雪糕好在種類夠多,可以叫一個所有味道都齊全的,至今有三十多個球,吃不完也要來一客。越南胡志明市的Fanny也有此等風味,他們還有獨特的人參果雪糕,所謂人參果,是一種南洋水果,褐色,很甜,是我小時最愛吃的水果之一。吃呀吃,吃到雪糕從兩邊耳朵流出來,這是西班牙人描述過癮的手勢。
還有烤乳豬,葡萄牙有一個小鎮,所有餐廳都是賣這種美食,如果你要我選中國烤乳豬和葡萄牙的,我還是會選後者,它的竅門在於把豬油塗滿豬的內側再拿去烤,這一點是中國烤豬做不出來的味道。
一提到葡萄牙當然還想到他們的砵酒,最老的砵酒在那邊喝也不是甚麼大事,價錢又便宜得令人發笑,買一個當地蜜瓜,把砵酒倒在裏面又吃又喝,是天衣無縫的配搭。去時選沙甸魚的季節,當沙甸魚肥時,是天下最美的味道,這時又得做西班牙人的手勢,從雙耳流出來。
玩播客
2020/10/07
瘟疫期間,不能讓它一天天白白浪費,還是要找點事來做,很多玩意兒都實行了,新的是甚麼呢?
想了又想,又和許多朋友談過,最後決定玩Podcast。
英語的這一詞,是由iPod和broadcast組合,中文被勉強地譯成「播客」,有許多人都早在十幾二十年前玩過,不是甚麼新主意。
最初是一架iPod就行,當今沒甚麼人用iPod了,都是iPhone和iPad的世界,總之架上了它,能看自己,就可以向外廣播。
已有無數人在玩,為甚麼有人會看你的?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如果懷着一開始就有大把人看,這個玩意就失敗了,內容當然是最重要,言之有物,就有人欣賞,慢慢來好了,反正這是一個被鎖在家裏的年代,盡量把內容做好它再說吧,其他想太多也沒有用。
看其他人的「播客」,一開始便自言自語,得到的第一個印象,是此君蓬頭垢臉,燈光又平淡,太不嚴謹。
我媽幾十歲時,起身洗臉之後還略施脂粉才走出臥房,這一點要學習的。
在家中已如此了,還說要出來「見客」呢。見群眾當然要打扮打扮才行,並不是愛美,而是對別人的一點尊重。
既然要做,就要好好地做,這是父親教我的,所以我不想在家裏對着鏡頭就做,而是要找個地方來實行,剛好生意上的拍檔劉絢強有個很大的辦公室,可以空出來讓我亂玩,再好不過了。
劉絢強本身是做印刷的,他在大陸有最精美的印刷廠,更結合了一群藝術家做展覽,這群人對燈光最有研究,請友好們來替我裝修一下門面,才是見得人。
至於內容,當然是想到甚麼講甚麼,一受限制了總是做不好,守着只談風月,不講政治的原則,任何題材都可大談一番。
單單是我一個人可能太過單調,劉絢強一家人參加了我的旅行團已有數十年,他一家人我也從小看着他們大,都當成親人了。
兩位女兒也從她們拍拖到生小孩,可以和她們談一些生活上的點滴,大女愛喝酒和美食,小的愛做甜品麵包,反正地方夠大,可弄一個廚房和烘焙室,一面談天一面做節目,較不枯燥。
用的是甚麼語言呢?大陸市場的話是當然說國語,但是這個直播我還是要面向香港觀眾,說粵語較為親切。
也做了一番研究,至今最多香港人看的是YouTube,節目放在它上面播放,YouTube在國內看不到,也可以選個平台在大陸播放,這還要進一步地商討才能決定。
也許組織一支隊伍,把節目打上字幕,讓聽不懂廣東話的人也可以看。
至於要叫甚麼名字,我現在還想不出,我從前做節目都是由金庸先生替我題字的,也許我會模仿他的書法寫上節目名。
十多年前盧健生介紹了我「微博」這個平台,我開始用心地玩,回答網友的問題,組織一百二十個字的微小說競賽等等,粉絲一個個爭取,至今已有一千零九十多萬粉絲,都是因為我發了十一萬條微博得來,如果我用同樣的努力,「播客」也能得到一些觀眾吧。
即使是微博,也都是以文字來溝通,文字是我的強項,雖然我做過《今夜不設防》和許多旅遊節目,但現身說法總不如文字的交往,這次又是我來和大家見面,還是要從頭學習的。
從前做節目時,如果喝多幾杯酒,膽子就大了,當今酒已少喝,酒量也大不如前,不能靠它來壯膽了,硬着頭皮頂硬上吧。
身體狀態好的話,會較有把握的,但人一疲倦,就不想多說話了,做這個節目,我還是有點戰戰兢兢的,不過也不去想那麼多了,要是不開始,只是口講而不實行,時間又浪費了。
要先得到大家諒解的是我的記憶力大不如前,有時會講錯話,有時時間和地點都會搞亂,總之我盡力而為,對得起各位,就對得起自己了。
寶
2020/09/30
請各位讀者再三原諒,我今天又要談串流Streaming中得到的樂趣了。
從前我很不喜歡在文中提到電視節目,認為這是沒有生活情趣的寫作人才會涉及,不然美食、旅行等等有大把題材,何必談這些躲在家裏才接觸到的東西?不過當今是例外,我們都為了疫情而被鎖在家中,電視的串流變為我生活的一部份,只有一談再談了。
還以為我自己很先進,會用新科技欣賞串流這種新媒體,但當我看到了《叢林中的莫札特 Mozart in the Jungle》,才知道我自己很落後,這個串流的電視節目早已在二○一四年就開始播出,我是多麼地後知後覺!
一共拍了四季,我不休不眠地追着看,像着了迷,每季十集,每集三十分鐘,二十小時的戲,我不一口氣看完不肯罷休,現在要鄭重地介紹給大家,千萬別錯過這顆寶石。
講的是甚麼?紐約的交響樂樂團成員的故事,這絕對不是人人喜歡的題材,實在小眾得要命,就連美國也只有紐約人能接受,當然紐約不是美國,紐約是獨特的,只有紐約那麼高文化水準的地方,才能製作出那麼標青的節目來,而香港,是最接近紐約的都會,相信也有人會欣賞。
製作團體的主幹是羅曼.哥普拉Roman Coppola,你猜對了,他是大導演哥普拉的兒子,蘇菲亞哥普拉的哥哥,作曲家卡米尼哥普拉的孫子,這家人都特別有天份,祖父留給他的音樂細胞,令他很小便與作曲家音樂家人們為伍,這個故事交在他手上的確是如魚得水。
他從小愛電影音樂和旅行,並不在乎擔任甚麼角色,認為只要能參與已是最大的幸福,經過他手的有《犬之島》、《大吉嶺特快車》等等片子。
看過了Blair Tindall寫的回憶錄《Mozart in the Jungle: Sex, Drugs And Classical Music》之後他就決定改編成視覺作品。電影不可能,因為只能縮成兩三小時,這部戲全靠人物描寫,串流媒體的長篇才能充份表現。也沒有甚麼強烈的故事結構,只是講樂團中的各個人物,慢慢描述,讓觀眾一個個地愛上他們,就成戲了。
主角是年輕指揮家,選中了Gael Garcia Bernal這位墨西哥演員來擔任,他在《The Motorcycle Diaries》和《Y Tu Mama Tambien》等片中已被西班牙語系的觀眾大受歡迎,許多名導演都很愛用他,選他的另一個理由是現實生活中真有其人,委內瑞拉指揮家Gustavo Dudamel得了無數的指揮家獎,教宗尤其愛看他的表演,他本人也組織兒童交響樂團,並擔任洛杉磯愛樂樂團的音樂總監,在這部戲中分分鐘看得到他的影子。
女主角Lola Kirke,本身也會吹「雙簧管Oboe」這種樂器,每天演奏是五六個小時。雙簧管是最難吹得精準的,交響樂團演奏時,是讓它來調準音調。這樂器我以前的文章中也提過,蘇美璐說是她最喜歡的,因為原著作者也是吹雙簧管,請她來演是理所當然。
講那麼多,如果不愛聽古典音樂的觀眾會不會沉悶?一點也不。劇中選的多是膾炙人口的曲子,而且每集只有半小時,也不能都奏得完,劇中聽起來恰到好處,對從未接觸過古典的觀眾聽來頗親切,而且會逐漸地愛上,全劇看完,等於上了一堂音樂課。
在第三季,加了Monica Bellucci,演出名女高音,影射Maria Callas,已經五十二歲的她,全裸演出,不覺衰老。
劇情中的人物都是敢做敢愛的,他們熱愛音樂,也熱愛人生,興之所至就來一下,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對,也是輕輕鬆鬆,看得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配角Bernadette Peters,她人長得漂亮,身材又好,歌唱得精彩,就是在好萊塢紅不起來,她演個交響樂團的經理人,不斷地為樂團找尋贊助者,又要安撫這群瘋子,演得出色,編導也找了個機會在劇中唱幾首動聽的歌。
演過氣指揮家的是Malcolm McDowell,大家還記得他是《發條橙 A Clockwork Orange》的男主角,這角色要不擇手段地死站在舞台上,在演藝圈中有很多這種人物,由他來演,特別活生生。
把藝術和娛樂糅合在一起的戲劇並不多,看了能提高自己的水準的更少,這部得獎無數的長篇劇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我看完也為製作人揑一把汗,不知道他們怎能說服投資者讓他們拍出來。
不過,到了最後只拍了四季,還是被腰斬,儘管眾多的觀眾為此不值,但事實歸事實,救不起來,拍不下去。
可惜呀可惜。
大家要看的話,當Prime Video會員吧,沒有幾個錢的。
君子國
2020/09/23
當你想不出要寫些甚麼,往菜市場去吧,總能找到一些可以發揮的題材,而且今天還有一項特別的任務,就是和雷太拍一張照片留念。
沛記海鮮在菜市場進口的第一檔,我已經光顧了幾十年,主人雷太在全盛時期擁有數艘漁船,甚麼名貴海鮮都能在她檔中找到,我喜歡的都是隨着拖網捕撈的一些雜魚,像七日鮮、荷包魚和不知名的,都是我最愛吃。
隨着年紀、她的魚檔賣的名貴魚越來越少,只剩下一些馬友和海斑,另外的老虎蝦和魷魚,是兒子的冰鮮店拿來的,但我還是不停地在她的檔口停一停,不買也打聲招呼。
今天,是她最後一天。兒子見她歲數大了,不忍心看她每天在這裏辛苦,請她休息休息,許多老顧客都不捨得,不過她也不是完全退休,收拾了魚檔之後,她會到侯王道在她兒子開的冰鮮店幫手,想念她的人可以到店裏和她聊聊天。
菜市場的檔主和顧客們交易久了,就會成為老朋友,這種關係可能會濃厚過家人,我住在九龍城,九龍城菜市場可以說是我家的一部份了,幾天沒去,小販們都會關心地問起我來。
和檔主們做了朋友,再也不必擔心買不到最新鮮的貨物,他們總會把最好的推薦給你,有時算得太過便宜,付錢時多加一點,對方不肯收,買的人更不好意思,大家推來推去,真像小時候書裏說的君子國。
蔬菜檔的二家姐,從前也不在菜市場,而是開在侯王道的一間店裏。一共有四姊妹,都是美人兒。四姊妹中有一位早走,另一位在家享清福,大家姐還在雷太魚檔對面賣菜,二家姐的開在另一邊,所賣的蔬菜最為新鮮,好處在如果想不出要燒些甚麼菜,她會不厭其煩地一一為你想好。本來二家姐也可以退休了,但她說是為了等兒子成熟接班,要多做幾年,我卻看她樂融融地,似是不肯呆在家裏。
最近香港政府為美化市容,請了許多街頭畫家,把九龍城的店舖都畫上彩畫,衙前塱道上的「義香荳腐店」就是其中之一,這家人由兄妹二人經營,畫家把他們兩人的大頭畫在門上。其他家也畫了,但都一早開店看不到繪畫,只有義香的畫最顯眼,那是因為他們的店開得最晚,通常要在中午期間才營業,開到傍晚就收檔,我最愛吃的反而不是他們的豆腐,而是大菜糕和涼粉,但不敢多買,因為妹妹不肯收錢,店裏也宜堂食,有許多老顧客經常停下,吃一兩件新鮮煎炸的豆品,或喝杯豆漿才繼續買菜。
再過去幾家也是經常光顧的「元合」,這裏是唯一可以買到潮州魚飯的店舖,但年輕顧客不懂得欣賞,魚飯種類沒有以前那麼多了,另一個原因是海鮮越來越少,一少就貴了,當今的魚飯沒以前那麼便宜,他們的炸魚蛋最為爽口,也有很多人喜歡。
街尾的豬肉檔和牛肉檔生意很興隆,豬肉檔的肉最鮮美,牛肉檔生意特別好,一到天氣冷就大排長龍,大家都買牛肉來打邊爐,我們都已成為老朋友,不買也走過去閒聊幾句,最常說的是來看看他們有沒有偷懶。
也不是家家都是老店,生力軍有來自潮汕的「葉盛行」,這是一家做大宗潮州雜貨的店舖,甚麼都有。我喜歡的是老香黃,即是一種佛手瓜醃製品,越老越好,所以叫成老香黃,我到夏天拿它來沖滾水,泡出來的飲品以前老人家說可以治咳嗽,也不知是否有效,反正我喜歡那個味道,到了深夜喝濃茶睡不着覺,喝老香黃水最好不過,從前要到潮汕才能買到,當今不能旅行,可以在「葉盛行」買到,實在方便。
同條路上還有老店「老四」了,一度發展得厲害,當今守回老檔口,賣滷鵝,疫情之中外賣反而生意越來越好,九龍城賣滷鵝的檔口不少,但「老四」還是品質最有保證的一檔,除了滷鵝,他們做的滷豬頭肉、滷豬耳朵和鵝腸等,都很受歡迎。
再走去就是「潮發」了,這家老潮州雜貨店甚麼都有,欖菜也是自己做的,我最愛吃他們的鹹酸菜,有鹹的和甜的兩種選擇。潮州甜品中的清心丸也可以在那裏買到,一度被禁止,因為用了硼砂,但這種小吃在潮州已存在了上千年。
隔壁是「金城海味」,在這裏買鮑參翅肚最安心,價真貨實,乾鮑也能代客發好,請客時加熱就行,要買陳皮的請儘管在店裏選購好了,有最好貨色。
折回侯王道,當然去「永富」買水果,當今除了高級日本蜜瓜、葡萄和水蜜桃之外,還有新鮮運到的雞蛋「蘭王」,要吃生的話盡可放心,雞蛋的包裝上有何時進貨的日期。
隔壁的「新三陽」是愛吃滬菜的人最愛光顧的,如果你想自己做醃篤鮮,他們除了新鮮豬肉之外,甚麼都會替你配好,按照店員的方法去煲,一定不會失敗,我還愛買他們新鮮做的油燜筍、鴨腎、烤麩等等小吃,有時會買些海蜇頭回來,用礦泉水沖一沖,再淋上意大利陳醋,百食不厭,你也可以試試看。
串流天下
2020/09/16
在家裏,電視節目無聊,好在有「串流」這兩個字救命,否則會悶出神經病來。
對不接觸科技的人來說,有沒有「串流 Streaming」也無所謂,對我這種愛看電影電視劇的人,簡直是救命恩人,現在天天靠它,才能入眠。
最典型的例子,也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就是Netflix了,當今的新電視機已替你安裝好,一按掣就能看到,不然在平板電腦或手機上從App那裏找到後下載即可,簡單得很。
Netflix是一個無底深淵,要看甚麼電影電視劇都有,當今,已是多得看不完。西方流行的笑話是:花在尋找你要看的時間,多過你想看的節目。
是的,Netflix太多,太雜了,之前節目不錯,當今已有粗製濫造的趨勢,有點麻木。還是推薦大家去看Prime Video吧,這是大集團亞馬遜出生的愛嬰,財勢雄厚,要製作甚麼節目都行,也不怕虧本,但他們不是鬧着玩的,眼光闊大而精準,實在來勢洶洶,是Netflix一大對手,把Disney、HBO、Apple TV拋得遠遠。
怎樣上線看呢?在App上找到Prime Video即刻可以下載,其他地區還要付月費,像台灣,月費也要5.99美金,一點也不算多,香港可以試看7天,之後收費和台灣一樣。
最初並不注重中文市場,許多節目並沒有字幕,打開了台灣之後便有中文繁簡體並用的字幕,但還不完善,用中文尋找片名,還是有困難,但對懂得英語的觀眾來說,一點問題也沒有,而且他們針對的,也是這類觀眾。
Prime Video雖然有各種別人製作的節目,但還是以本身的為主,我當今追的有《漫才梅索太太 The Marvelous Mrs. Maisel》和《律政巨人 Goliath》,前者從二○一七年開始播第一季,到二○一九年播第三季,第四季又即將來到,講一個棟篤笑(Stand-up comedian)的人物,觀眾會一步步地喜歡上她,一直追看下去。
當然,要欣賞這個電視劇的人首先要喜歡紐約,它以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為背景,和《廣告狂人Madman》是孿生兒,一部嚴肅,一部是喜劇。
女主角梅索夫人被先生拋棄後自力更生,以表演棟篤笑為生,創出自己的一個天地。製作甚肯花錢,不管在服裝和道具上都很考據,一一重現。又加上當年的流行音樂,時而載歌載舞,像在看一齣音樂劇,喜歡上了就不能罷休。
她身邊的人物,像經理人Alex Borstein和她的父親Tony Shalhoub的演技更無懈可擊,後者演的神探Monk,早已深入民心,演甚麼像甚麼。
此劇得獎無數,艾美獎更不在話下,幾乎所有電視獎都能囊括,還沒看時不能了解有甚麼那麼厲害,一看上癮後便能明白製作人兼劇作者的苦心,Amy Sherman-Palladino的父親是個棟篤笑演員,她當然受了影響,細心地考據和重視當年的資料,活生生地描述出來。
當然,如果能夠了解猶太人文化,那麼看來更會津津有味,美國娛樂界被猶太人控制,他們會在電影電視上一一滲透他們的習俗和人文關係,像割禮、婚禮和家庭聚會等等,一有機會,便拼命介紹,這種手法並不討厭,可以引起其他族群的共鳴。
另一套《律政巨人》依靠好演員支撐,主角Billy Bob Thornton的演技是毫無疑問的,講一個落魄的律師怎麼去為無辜的受害者爭取公道,主角強,配角要更厲害才行,演他對手的是William Hurt,以前常演謙謙君子,這部劇中當反派,精彩絕倫。一共三季,每季都值得追看,男主角煙抽個不停,是不是有煙商私底下贊助,不得而知。
除了這些,令人追的還有《邋遢女郎 Fleabag》,講一個不修邊幅的女子怎麼在這社會生存下去的故事,當然很受女權份子歡迎。
也不是全部嚴肅,《復原 Undone》由動畫片《Alita》的製作班底創作,用奇異的畫面來講八個短故事,很受觀眾歡迎。
《傲骨博斯 Bosch》是另一個拍得很好的片集,男主角Titus Welliver之前專扮反派,想不到演技如此精湛。
《歸國 Homecoming》就用上大明星Julia Roberts了,講退伍軍人的創傷,相當地沉悶,但如果沒有別的,為了女主角也可一看。
《黑袍糾察隊 The Boys》是反當今的英雄,娛樂性較高。用科幻大師Philip K. Dick小說改編的《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也很好看。
如果你能接受印度片,Prime Video上有不少印度作品,他們看準了印度這個龐大的市場,又不會有諸多的限制,可以看的節目無數,是眼光獨到的。
平台上還有很多供應給小孩子看的節目,較為反傳統,用來搶迪士尼的觀眾。
有「串流」實在好,當今的科技還不成熟,等到5G、6G,幾秒鐘就可以下載一部片的話,所有的好萊塢電影和中國舊片都能即刻看到,到時又是一個熱鬧的局面。
電影火鳳凰
2020/09/0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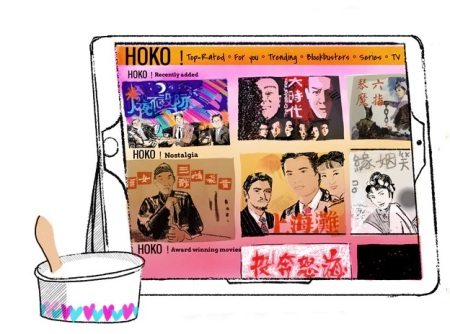
在一般觀眾眼中,《摩登情愛 Modern Love》只是一部清新的愛情片集,由亞馬遜的串流平台Prime Video播出,最近在網路平台上點擊力極高,絕對是不可忽視的小製作。
我看到一個革命性的創舉,如果香港電影能走上這條路,將是一條光明大道,令已經死去的香港電影重浴火燄,變成一隻不死的火鳳凰。
先介紹這部電影,它是改編自《紐約時報》的專欄,敍述發生在紐約的八個小故事,每一集都是三十分鐘,去探討愛情、友情和家庭。
第一集叫《當門房變成閨蜜 When the Doorman Is Your Main Man》,講住在公寓中的一個單身女子,在她生命中最可靠的朋友是一個門房,不管天晴天陰都能像家庭成員一樣照顧着她,他向她說:「我幫你看男人時,是看他們的眼睛。」
單身女孩人生經驗尚淺,她的男友離她而去,她獨自生下了一個孩子,看更一直在她身邊鼓勵和支持着她,沒曲折的愛情故事,但有強烈的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第二集講一個網上婚姻介紹所的老闆,自己卻得不到伴侶,直到他遇到一個青春已逝的記者,看到她失去愛人的經驗,才了解怎麼去追求真愛。題名為《當八卦記者化身愛神邱比特 When Cupid Is a Prying Journalist》。
第三集《愛我本來的樣子 Take Me as I Am, Whoever I Am》講一個躁狂症女人,怎麼走出這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四集《奮戰到底 Rallying to Keep the Game Alive》講一對已婚互相沒有話可說的夫妻,怎麼透過打網球去維持這瀕臨破裂的婚姻。
第五集《中場休息:醫院裏的坦誠相見》故事和題名一樣,講一對男女在約會中發生的突變,女的一直在醫院中照顧男的,兩人產生的感情。
第六集《他看起來像老爸 這只是一頓晚餐吧? So He Looked Like Dad. It Was Just Dinner, Right ?》講公司裏的小女職員和她的上司的一段感情,起初以為對方只是一個像自己爸爸的人物,後來怎麼改變主意去愛他。
第七集《她活在自己的世界裏 Hers Was a World of One》講一對同性戀者怎麼去收養一個嬰兒的故事。
第八集《比賽來到最後一圈 變得更加美好 The Race Grows Sweeter Near Its Final Lap》講在跑馬拉松的一個美國老女人,愛上了一個亞洲老男人,兩人一起競跑,但他先走了一步的故事。
單單看這些片名,已知道一般公映的好萊塢片子是不會用的,現在只在串流上放映,打破了被高昂發行費的限制,自由奔放,想怎樣題名就怎樣題名。
故事也不完整,一般觀眾會認為沒頭沒尾,但不要緊,你不必花錢去看,亞馬遜的Prime Video特別聲明這是零觀賞費。
也不是完全由無名演員出場,紐約有很多演員願意收取很低的出場費去完成一個自己能發揮的機會,故演員表只有Anne Hathaway、Tina Fey、Catherine Keener、Andy García等,其他主要演員也許你沒有聽過,但都是熱愛電影的人士,有我喜歡的金髮小女孩Julia Garner,此妞非常拚命,盡量爭取演出機會,二○二○年拍的《The Assistant》全片製作費才一百萬美金,所得片酬應該比她的電視片集《黑錢勝地(Ozark)》少得多。
演婚姻介紹所老闆的是印度演員Dev Patel,他從《貧民百萬富翁》開始就演過多部重要的電影,此片中他的角色已跳出國界。
另外的名演員也都不是因為錢而來,也許是他們認為自己是紐約人,應該為宣揚紐約做多一點事,而且,此片已得到很多電視劇的獎狀提名,得到單元劇的男女主角獎機會極高,大家都願意參與一份。
話講回來,如果有任何投資者夠眼光,就應該去辦一個中國人的串流平台,全世界的華人集中起來,市場已無限大的,先出資買舊的電影和電視片集,再製作一些清新的電影打頭陣,將是一個打破傳統電影院上映的機會,至於人才香港有大把,黃金年代的功夫片、殭屍片以及各種富有娛樂性的片子,將會得到重生,這個市場是因為得不到創作自由而滅亡的,只要讓大家放手去幹,一定能夠殺出一條血路。
串流製作,已經在美國定型了,也證實可以成功,大家可以打破明星制度,不必付巨額去請他們,有才華的年輕人多的是,串流電影上不需要大牌演員來保證票房,而且一大堆老演員都等着開工,降低片酬來演出,是他們樂意去做的事。
當今Netflix、Prime Video、Apple TV、HBO、Disney等等都已進入戰場,瓜分好萊塢的市場,我們還等甚麼?
西瓜罩
2020/09/05有時候,逛百貨公司,是一種消磨寂寞的最好辦法。雖然是陪別人走走,但自己也得尋找樂趣。
走進女裝部,友人看別的東西,我們可去研究香水,內衣部門更好玩,要不猥瑣, 目光充滿自信,甚麼地方都能去。
踏上三樓,整層都在賣女性內衣,墨爾本的百貨公司比香港大上十倍。
地方大,選擇自然多,晨褸、睡袍、睡衣、腰封、褲襪、底褲和胸罩。種類最多的,當然是胸罩了,一年有好幾億的生意。
一般的胸圍,價格由港幣一百元到一兩千元不等,顏色有:白的、黑的、紅的、藍的、紫的、銀灰的,也有皮膚色的,有些薄如避孕套,有些厚如鞋底。
運動家型的、良家婦女型的、情婦型的、變態婆型的和剛發育型的,應有盡有,任君選擇。
客人並不一定全是女性,各個年齡群的男子也到這部門購物,可以買來送女朋友、老婆、 女兒、情婦,甚至老媽子或外母大人,以胸罩當禮物,行李包不超重,價錢合理,物輕情重,何樂不為。
走完一圈,正想離去。看見一個四百磅的大肥婆,搖搖擺擺地走了過來,目光不禁隨著她移動,見她一個箭步,走向她熟悉的攤位,從架上一手拿了一個倒吊著的白色通花大胸圍,試也不試,就到櫃台付錢。
充滿好奇心,即刻到那個角落看看。
原來貨架的乳罩,都是為特異身材女士而設,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
二十八吋不算大呀?
「澳洲的尺寸,是從十、十二、十四算起。」售貨員親切地解釋:「等於別的地方的三十二、三十四和二十六了。」
「最大的呢?」我問。
「剛才那位女士選的不是最大的。」她說:「最大的是二十八,等於你們的五十。」
嘩。
至於是甚麼杯呢?當然不是茶杯囉。
澳洲的杯和香港的杯卻是統一的,用A、B、C、D來代表。杯怎麼量呢?很簡單,由女人的乳首開始計算,下半個乳房和軀體之間的距離,便是杯的位置。換句話說,乳首和背部加起來叫E線,軀體叫F線,E線大過F線一吋,即屬A杯,大過二吋,就是B杯,大過三吋,便是C杯,大過四吋,變成D杯了。
還是搞不清楚嗎?讓我慢慢解釋,有些女人虎背熊腰,軀體大得不得了,但乳房卻很小,也可似穿三十八吋,但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三十六,如果有ABC杯來量,那就原形畢露了。
還是不懂?唉,馬馬虎虎算了。
東方女人多數發育不足,穿著A杯,有的還可憐到要著最小三十AA杯呢。如果能有D杯級數,已屬犀利。西方女子,特大是殺死人的F杯!
售貨員拿了一個二十八F的給我看。這個五十吋的罩罩,用軟尺一度,直徑足足十二吋,深度七吋,問你怕未?
此大胸圍布質極差,上半球部份有通花的繡織,下半球是塊白布,底有鐵線箍住,中間還有一個俗氣的蝴蝶結,亮晶晶地閃著。乳罩帶子普通的只有一公分,但此怪物有三倍的三公分,可以伸縮。背部的鐵扣,通常只有一至二個,但它有六個排著隊。
研究了一輪,不買不好意思。
「就要兩個吧。」我向售貨員說。
「謝謝。」做成生意,她滿高興地問:「送給您太太的吧?」
呸呸呸呸呸。
拿回辦公室去,大家都嘖嘖稱奇,樂了一大陣子。
成龍也圍過來看,我解釋ABC杯的道理給他聽。
「不懂!」他搖頭走掉。
說也是的,會脫就是,懂得那麼多有甚麼用?
翌日,逢禮拜休息,工作人員都拿了相機,到維多利亞市場去拍照留念。
「不如改變一下,拿個錄影機去拍吧。」我說:「拍完翻錄,每人一盒,更有紀念價值。」
眾人贊成。
去市場逛完之後,買了雨個大西瓜,裝進那大乳罩中,叫同事當菜籃提著。
我先把錄影機鏡頭對著過路人拍特寫,看見那西瓜罩,每個人都捧腹。
再拍提著西瓜罩的同事大搖大擺地走過,待稍後剪接成片段。
但一個笑料不夠,必須追擊,才能保證票房,又叫道具的兩個長得像孖生的兄弟粱銳能及梁銳棠抱在一起,頭上各一杯地戴那個乳罩當帽子,扭著屁股招搖過市。
路人笑得跌倒地上,拿錄影機的手也提不穩,跟著笑得跌倒在地上。
蔡氏出品,必屬佳品。